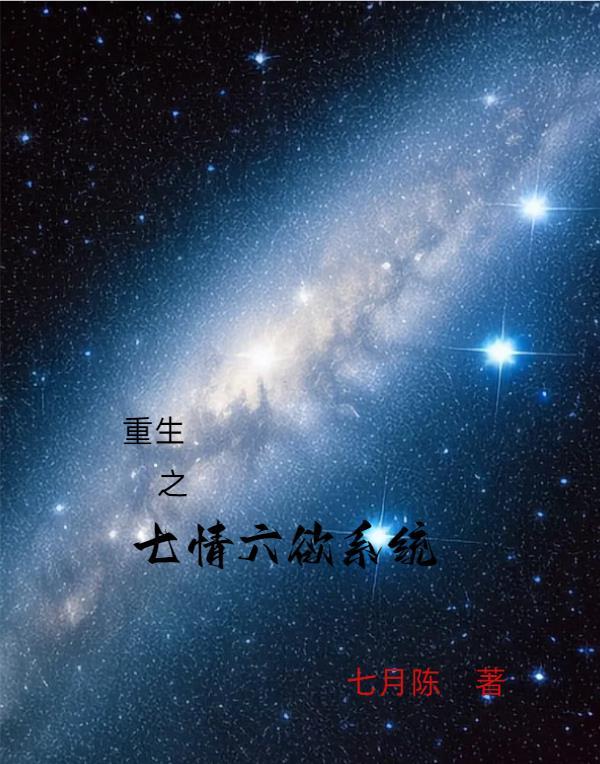笔趣看书>炮灰觉醒后,在年代文里乘风破浪 > 第13章 书里没写这一段啊(第2页)
第13章 书里没写这一段啊(第2页)
她一边和方茴说话,一边手脚麻利的捡起地上放着的串了一半的门帘儿,开始快的串起来。
“这是草珠子,我们这也叫尿床珠。
眼见就要入夏了,苍蝇蚊子都活泛儿起来,整日里嗡嗡嗡的,扰得觉都睡不好。
这不,我就寻思着串扇门帘儿,好看又实用。”
方茴抓起一把草珠子,手里凸凸起起又圆润微凉的触感,让她觉得分外熟悉。
丁婆子还以为方茴不知道这东西,毕竟人家是从城里下来的女知青,所以她喋喋不休的给方茴讲着草珠子。
“这东西呀,在后坡那大野地里长了不少,割上一抱回来就能串一扇门帘儿。
出来进去的时候,草珠子碰撞在一起,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可好听了。
我可跟你说,方丫头,在咱们这,关于这尿床珠还有讲究呢。”
方茴好奇,忍不住问。
“用草珠子串门帘儿还有什么讲究?难不成还得挑日子?”
丁婆子点着方茴的脑门,语气里有着难以掩饰的亲昵。
“你这丫头,又不是定亲,挑什么日子。
在我们这,男人们是不能碰这尿床珠的,就连几岁的男娃娃都不行。”
方茴睁大了双眼,还有这讲究?她还真没听说过。
“这是为什么啊?”
丁婆子嘿嘿一笑,有些神秘兮兮,这让方茴也跟着莫名紧张起来。
“为啥?还不是因为它的名儿,若是男人们碰了这尿床珠,晚上回去指定尿床,别管他多大岁数。”
“真的?”
丁婆子开怀大笑,“真的不真的,我倒不知道,不过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反正在我们大岭山,男人们是不碰这东西的。”
老支书听见外头的动静,也拎着旱烟杆子从屋里出来,连带着一直在灶堂里忙活着晚饭的平嫂子也出来了。
“方丫头过来了。”
老支书一张老脸上笑开了花,他们大岭山那么多城里来的女知青,他最得意的就是方茴。
“老支书都话了,我还能不过来?不过——杨叔,今晚有什么好吃的呀?”
方茴来老支书家吃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和杨家的人都熟得很。
每每在家里,她就称呼老支书为“杨叔”。
平嫂子——也就是生子娘,是个心里藏不住话的,平时就大大咧咧惯了。
她听见方茴问今晚吃什么,立即就挥着手里的菜铲子答话。
“妹子,你有口福,今儿我们家炖鱼。”
哟,还那还真是改善伙食了,只不过这鱼是从哪来的?
老支书嘴角含着一抹心满意足的笑,将手里的旱烟杆子往石桌子上磕了磕,烟灰瞬间就掉落满地。
“还不是我家杨顺回来了,他得了探亲假,回来特地在供销社那扯了几尺布,又买了一条大鱼,说是孝敬我们老两口子的。
你说说,就是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
他去接个部队的领导,说是一会儿就能回来。”
老支书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虽然话里的内容都是在责怪小儿子胡乱花钱。
可那脸上的神情,和说话的腔调,无不是在像方茴炫耀着自己有个好儿子。
方茴也不是那不开窍的人,就着这个话题夸了老支书的小儿子好几句。
直把老支书两口子夸得心花怒放,一个劲儿的说她长了一张讨巧的嘴。
老支书的小儿子,书里也只提到过几句,和她一样,就是个可有可无的路人甲,听说是在部队上当兵。
他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书里好像从没写过这一段儿吧。
正在这时,院子外响起了说话声。
生子欢快的跑了出去,一边跑嘴里还一边不停的嚷嚷着,“是小叔!小叔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