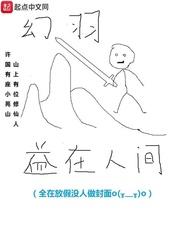笔趣看书>裴少帅的心尖宠 > 第3章 她还是回来了(第1页)
第3章 她还是回来了(第1页)
乘坐黄包车到达了火车站,锦书亦步亦趋跟着陈副官,车站人头攒动,陈副官和其他两个随从伸手将锦书护在身侧。
有一个随从让锦书印象深刻,因为他叫谢鼎,一身中山装,一米八几的个头,眉宇间很是煞人,再看那醒目锃亮的头顶,果然人如其名,只有二十四岁的年纪,头顶上早已光秃秃一片。
这一阵子都是他和另一个名叫阿武的的随从一直照顾她左右,他们身手都不错。
而陈副官偶尔北平杭州往返的,所以第一眼她就记住了这个叫谢鼎的男随从,记得谢鼎也半开玩笑调侃了一下他自己,说:“我觉得我的名字取坏了,若是取谢长名字,说不定我的头不至于年纪轻轻掉光了。”
锦书听后,觉得这人看上去五大三粗,说话倒是幽默。
终于上了火车,锦书回头看着杭州站台,她心底轻轻说:“苏澈,等我三年,三年后我回来,然后守你一辈子。”
火车动驶入轨道那一刻,出低沉的轰隆隆声响,火车头冒着白烟般的蒸汽,然后化作一团烟雾随风消失在空气中。
锦书坐在头等车厢的车窗边上,单手托腮,眼睛游神般看着外面。
陈副官放下行李,说:“6小姐,我就在隔壁,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叫我,谢鼎和阿武在门口守着,有什么也可以随时叫他们。”
锦书似没有听到,出神看着窗外,眼神空洞。
陈副官抿了下唇,便转身打开门出去,在关上门的时候,陈副官又看了眼6锦书,那单薄的身子,那空洞的眼神和苍白的脸色,如果不是她有呼吸的坐着,真以为她是一副游魂,稍不注意随时就会消失不见。
他永远不会忘记苏澈去世后,她跪在苏澈的灵堂前,不哭不闹,仿佛像个局外人,偶尔她会半趴在那具冰冷的身体上,将脸贴着那个冰冷的脸,闭着眼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即便睁着眼,那眼神也是没有灵气的,空洞无光,身如槁木,像一个孤魂野鬼,随时随刻都会随爱人离去一般,他看得心惊肉跳。
此次他来杭州,是他们少帅的意思,少帅说:“去吧,她一个女孩子独自一人处理起后事总归没有经验不方便,料理完后事将她带回北平。”
因此灵堂所见以及日后在苏宅点点滴滴,锦书的种种漠然寡言的样子,看得他提心吊胆,深怕她做出什么傻事来,到时候他可不好向他的少帅交代。
这七七四十九天,他时刻安排跟他一起来的手下轮流值守看着她,她足不出户,他们只能轮流做饭给她吃,至少将她带回北平是个活生生的人交到少帅手中,他们也算完成了任务。
三天后火车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了北平,下了火车,一股凉意直接扑面而来,那风像刀子似的直接刮在锦书脸上,生疼。
而身子忍不住打了个寒噤,这才十月下旬,若是到了隆冬季节,北平岂不是更是寒意十足?
不过她也曾生活在北平数年,因此也了解北平气候,今天好在穿了件斜襟夹袄衫。
“6小姐,车子已经在站台外等着了。”陈副官说道。
锦书点了点头,抬头,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喧闹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像鱼儿样从四面八方游来,又匆匆地向四面八方游去。。。。。。
锦书看着站台人来人往的人群,一时恍惚,仿佛站在十字路口,她突然不知该走向哪里?
再看如今的北平火车站,已不复当年幼时模样。
记得那年她八岁跟着十四岁的苏澈第一次坐上北平的火车去往杭州城,那时的北平车站还没有像现在这般大,这般宽敞。
那年前她是多么决绝坐上火车,想着她从此以后不会在踏入北平半步,可没想到时隔多年后,她还是踏上了这片土地,还是回来了。只是一想到让她回来的原因,她的心慢慢沉落,眼里的光逐渐黯淡。
“6小姐,这边走。”陈副官拿着行李箱对又失神的锦书轻声说道。
锦书这才回神,立即随着陈副官走出了站台,其他两个随从身后脚步紧跟。
刚出站台通道,因为人群摩肩擦踵,锦书被身边一个脚步匆匆的行人给绊倒,陈副官心惊,眼疾手快去扶锦书,总算不至于锦书狼狈摔倒在地,只是她的额头被刚才行人肩上扛着的木质箱子给蹭破皮了,流出了血。
行人又惊又怕又不好意思,不停向锦书道歉,陈副官大声呵斥那个行人走路不长眼,倒是锦书摇了摇头,说:“不碍事。”然后对陈副官说:“小事,我们走吧。”
陈副官这才作罢,只是不免有点担心若是他们少帅看到6小姐额头的伤如何是好?
“6小姐,待会儿路过西医药店,我去买点消炎药处理一下伤口吧。”陈副官说道。
“只是蹭破皮而已,无妨,”锦书淡淡而道,说着从衣襟袖里掏出帕子擦了擦额头的血,触碰上去,很疼,锦书才现额头蹭破的伤口似乎有点深,血擦了擦还继续流出来。
出了站台,锦书就看到前方停着一辆黑色福特汽车,陈副官加快步伐,想上前打开后座让锦书坐上去,只是没想当他打开后座的时候,愣住了,他们的少帅竟然在后座?
少帅怎么来了?他不是在电报里说让自己下了火车站直接带6小姐回雨轩山庄吗?可没说他亲自来接6小姐啊?
“少帅。”陈副官恢复惊愕忙恭敬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