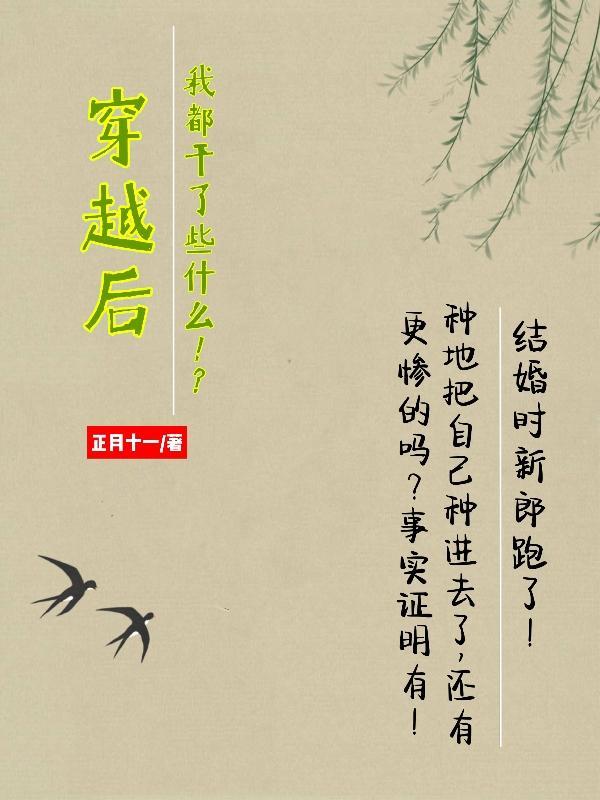笔趣看书>带着手机重生2007 > 第63章 年11月26日夜 死亡诅咒(第1页)
第63章 年11月26日夜 死亡诅咒(第1页)
兄妹俩从望湖茶厂离开后,就去了武汉,没有大人跟着,兄妹俩彻底放飞,东湖鸟语林喂鸵鸟,户部巷吃小吃,黄鹤楼拍照、长江大桥看夜景,晚上又吃了一顿烧烤才回酒店。
两人住在一家四星级酒店,要了一间套房,季疏缈睡在里面房间,季书朗睡在外边客厅的沙上。
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季疏缈这个年纪住一间房实在不安全,容易被人扛小猪崽似的扛走。
河北,谦华砖厂。
这一批临时搬运工正在结算工钱,季振华从办公室出来,哼着土味老歌,脚步轻盈地向着厂外走,他要去街对面的饭馆打包两个硬菜,中午和岳父、姐夫喝上一杯。
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拉住了他的衣角:“差五十块。”
季振华:“你找财务。”
正在给工人工钱的财务听到,扬起头喊了一声:“不差他的,华总别信他。”
“那没办法了。”季振华耸了耸肩,继续往厂外走。
一柄雪亮的刀刃刺进他的腹部,三角眼悬针纹的男人笑了一下,转身消失在人群里。
季振华低下头,看到自己的鲜血汩汩往外流。
他倒下去的那一瞬,被无限慢放拉长,季振华看到厂房里的电子日历——2oo7年11月3o日。
是他上一世的死亡时间。
季疏缈猛然坐起身,胸腔里的心脏怦怦狂跳个不停,整个人陷在惊恐后的歇斯底里中,眼泪像涌泉似的流着。
她轻轻动了动自己僵麻冰冷垂在身边的双手,忽然浑身战栗起来,不停地打着寒颤,苦丝丝的东西从胃里往外涌,季疏缈只觉得恶心,她想把身体里那种无力的憋人的恐惧吐出来,又始终做不到。
房间外响起开门关门声,声音不大,却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季疏缈从恐惧悲伤的冷潭中抽身,吸了吸鼻子,擦干净眼泪,下床打开门。
“还没睡?”季书朗一愣,朝她招了招手:“睡不着来陪我看球。”
电视里正无声地放着nBa比赛,季书朗拿起遥控器关掉静音,随手拿起沙上的抱枕扔在地毯上。
季疏缈挪过去,靠着沙坐在抱枕上。
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两袋鸭货、几罐啤酒,季书朗刚刚开门就是在拿这些,他给了小费,让酒店的工作人员买的。
“做噩梦了?”季书朗问。
季疏缈伤心委屈地“嗯”了一声。
“小可怜。”季书朗揉了揉她的脑袋,“还是小孩子呢,别什么都往心里装。”
“你们在我才是小孩子。”
没有家人,我就是个没人要的小破烂。
季疏缈又忍不住想哭,上一世姨妈去世以后,她见姨父和朗哥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见面他们都要伤怀许久——季疏缈长大后的眉眼,实在太像秦蕴了。
失去至亲的伤痛又岂是时间能够疗愈的,那心上血淋淋的伤口,只会在裹挟着砂砾的潮汐冲刷下,变作坚不可摧的伤疤,向内生长出细密的尖刺,扎进心脏肌肉里,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隐密作痛——要是她他还在就好了。
季书朗温声道:“别怕,我们都在呢。”
“我们明天去河北吧,我想爸爸了。”季疏缈抿着嘴,声音中还带着些许哭腔。
“好。”季书朗打开一罐啤酒递给她,“在烧烤店就想喝了吧?想喝就喝呗,不用那么难为自己。”
季疏缈犹豫了一下,接过啤酒捧在手里:“秘密。”
季书朗轻笑一声,拿起手里的啤酒和她的碰了碰:“秘密,我不告诉他们。”
季疏缈喝了一大口冷啤酒,舒服地喟叹出声:“我要吃鸭脖。”
季书朗眼一横:“自己拿,没长手吗?还要我喂你?”
“我不想弄脏手。”
季书朗没好气地把一次性手套扔给她。
季疏缈:“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