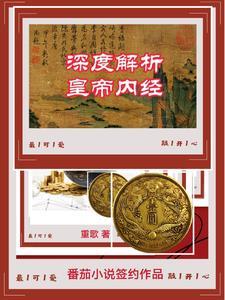笔趣看书>预谋出轨+番外 > 第11页(第1页)
第11页(第1页)
她-----陶涛,也是有人关心,有人疼的。她妈妈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初中文化,和爸爸是青梅竹马。虽然她患有轻微的先天性心脏病,但爸爸还是勇敢地娶了她,她也很勇敢地冒着生命危险为他生了个孩子。怀孕四个月,去医院做b超,医生悄悄说是个儿子,结果到分娩那天,护士从产房抱出个女儿。爸爸慌乱地揪着护士,问有没抱错?护士愤怒地告诉他,今天出生的都是女孩。但也就是有一刻的失望,当小陶涛躺在妈妈身边哇哇大哭时,爸爸就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我家闺女嗓门真大。生完孩子之后,妈妈的身体到比以前健康了,但爸爸仍让她在家呆着,啥事都不要她cao心。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一接通,便听到里面传来哗啦啦地麻将声。&ldo;小涛,&rdo;妈妈乐呵呵地笑着,&ldo;想妈妈了?&rdo;&ldo;妈,你少打点麻将,对腰不好。&rdo;陶涛本想对妈妈撒个娇,可话到嘴边,出来就变了。&ldo;我的身体我有数。你在家还是在公司?&rdo;&ldo;在家!&rdo;陶涛委屈地撅起嘴。&ldo;妈妈……我有点讨厌华烨了……&rdo;&ldo;我知道你又任性了,唉,结了婚,可不比和爸妈过,要懂事,多体贴男人。&rdo;每逢她和华烨生气,向妈妈抱怨,妈妈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华烨那边,在他们眼里,华烨是无法挑剔的佳婿。&ldo;算了,当我没说。妈妈,我饿,你过来给我做南瓜面疙瘩。&rdo;&ldo;陶太太,快来,该你拿牌了。&rdo;她听到有人在叫妈妈,麻将声震得耳朵发嗡。妈妈好声好气地商量,&ldo;小涛,今天咱不吃南瓜疙瘩,星期六妈妈过去给你做,做很多,你晚上到外面去吃好吃的,嗯?&rdo;她能说不好吗,不情愿地挂上电话,感到眼睛里热热的,恨妈妈见赌疏亲。抬起手臂拭泪,疼得直抽气。暂时又睡不着,信手把翻着的《张爱玲选集》拿了过来打发时间。一翻开就看到几行字。&ldo;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lso;c黄前明月光&rso;。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rdo;她冷笑了下,原来男人就是贱呀,不管红玫瑰还是白玫瑰,娶不到的就是好的。最好能坐享齐人之福,又能娶一个贤淑的妻子,又能拥有一个火艳的情人。可是万一再出现一个神秘的黑玫瑰或娇艳的黄玫瑰呢?男人的心真大,什么时候总能腾出一个位置放别人。可是这些事的发生都有个前提:久而久之,也就是婚姻专家们常挂在嘴边的&ldo;七年之痒&rdo;。七年,潜伏的细菌才开始发作,她和华烨结婚还没有七个月,这细菌提前发作了?应该不会吧!华烨一向清冷,又不是今天才这样。她在心中轻轻宽慰着自己。屋里太安静,仿佛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她倚着c黄背上发着呆,倦意渐渐袭来,她慢慢地探进被窝,带着疑惑睡着了。睡到半夜,忽然有温热的气息袭上后颈,细密缠绵,她迷迷糊糊地嗅到呛鼻的酒气。&ldo;你又喝酒。&rdo;她下意识咕哝了一声,声音含糊不清,早忘了白天内心的纠结,身体本能地翻了个身,习惯性地抱住,将脸贴上去。不等她沉入梦乡,就感到一只滚烫的手游移进了她的睡衣,开始缓慢上移,同时,唇再度凑上前来。她这才有点清醒,但眼睛仍不肯睁。华烨的呼吸近在耳侧,那样清晰分明,低低回荡在夜里。灼热的是他的吻,细细密密,在黑暗之中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地落在她的后背和颈边,有一种干燥的温暖。身体就这样被熨帖着,这份温暖甚至穿透皮肤印上血管,让其中的每一寸血液都开始灼热沸腾。她低喘一声,情不自禁抱紧他,攀着他坚实有力的背脊,迎了过去。身子如过电般地颤栗着,连睫毛都在微微颤抖,她口干舌燥,意识模糊,如同突然脱了力,只余下轻微的喘息。华烨今晚带了几份狂野和猛烈,抓紧她的手时,碰到了手腕,她叫了声&ldo;疼&rdo;,但很快,快感如溶浆湮没了她,她努力咬着牙,呻吟声仍然细碎传出。他一下下冲撞着,深入她身体。同时吻向她的唇,撬开牙齿,吞噬着她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