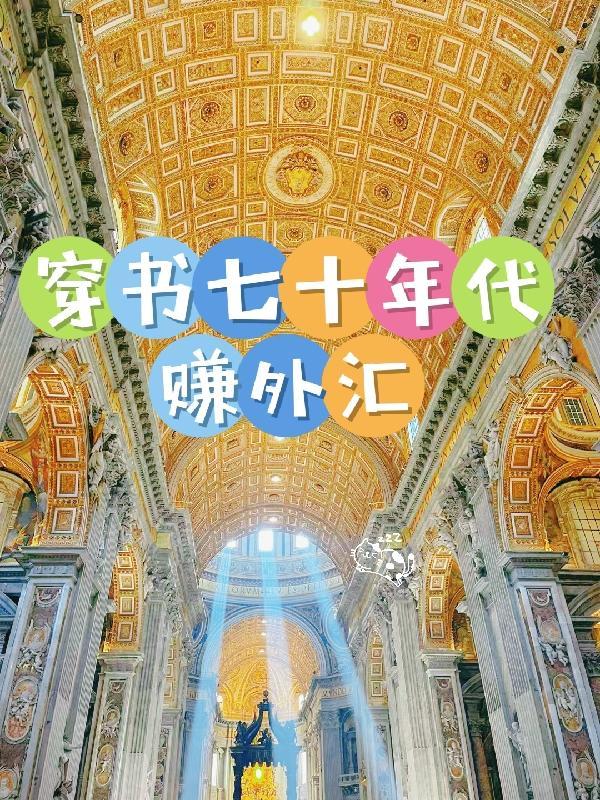笔趣看书>重生二嫁东宫,太子日日宠我 > 第21章 宴席(第3页)
第21章 宴席(第3页)
即使李寒玥笑得再得体,帝京的世家夫人也是不愿意自降身份,与妾室打交道,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也不便表露出来,总不好让人强撑病体出来陪笑吧?
魏郡公夫人全程冷着脸,暗自啐道:“小贱人,插根鸡毛,就以为自己是个鸟了?”
魏郡公夫人真是越看越气,实在看不下去了,索性孤身闯入后院,找姜柟好好骂骂这贱人。
“魏夫人,郡王妃受了风寒,实在是起不来了,怕把病气传出来,不便见客!”李寒玥赶忙追上去,将人拦下。
“我身子骨好着呢,不怕病气!”魏郡公夫人来势汹汹,推开李寒玥。
“郡王爷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后院,魏夫人是客,应客随主便,无请硬闯后院,便是失礼!”李寒玥叫来几个看院的婆子,一起堵住了魏郡公夫的路。
“原来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啊?妾就是奴!你好大的胆子,也配跟我叫嚣?我今日来是看着郡王妃的面子上,你竟敢拦着我不让见?”
“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们郡王府才惹人笑话!改明儿,我非要让我家郡公参你谢霖一本!真是气死我了!”
魏郡公夫人肺都要气炸了,偏偏那几个婆子身强力壮,拦着她,完全没有进入后院的可能,只能叉着腰破口大骂。
“罢了!”谢霖硬着头皮,拉李寒玥离开,丢下一句命令,“来人!郡王妃身染恶疾,把院子给我看住了,谁都不许进来!”
南凌郡王府为世子大宴宾客,因为谢述是太子殿下宁愿颜面尽失,也舍不得摔死的孩子,又是皇后娘娘跟前新晋的红人,受邀的帝京勋贵无不到场祝贺,热闹非凡。
谁都想看看这位空降的小世子,有何过人之处。
水榭凉亭,前厅后堂,到处都是人,下人忙得飞起。
所幸偌大的姜家只派了姜淮前来,谢霖将老丈人请进主院书房,拿出了压箱底的字画。
姜淮一眼相中,爱不释手。
“岳父大人若是喜欢,拿走就是!”
“这如何能行?我岂能夺人所爱?”姜淮笑着摆手。
“您将爱女许配给我,我已感激不尽,这些本就是为了岳父搜罗来的!”谢霖笑着恭维,见姜淮一脸满意之色,叹口气。
他话锋一转:“不巧,柟儿水土不服,病倒了,实在起不来,我舍不得她操劳,便让她歇着了!”
姜淮笑意微收,默默将字画收起,装入盒中,淡声道:“人吃五谷,哪有不生病的?她既病了,好好休息就是!那这些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主要你祖父喜欢,他见了高兴!”
两人相视大笑,谢霖宽了心。
“能讨祖父欢心,我这些银子就不算白花!”
“只有这些吗?还有没有别的……珍贵物件?”
“……”谢霖怔住,真没想到,姜家如此好应付。
宾客尽数到场,却迟迟不见主母姜柟,只一介妾室在主持大局。
即使李寒玥笑得再得体,帝京的世家夫人也是不愿意自降身份,与妾室打交道,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也不便表露出来,总不好让人强撑病体出来陪笑吧?
魏郡公夫人全程冷着脸,暗自啐道:“小贱人,插根鸡毛,就以为自己是个鸟了?”
魏郡公夫人真是越看越气,实在看不下去了,索性孤身闯入后院,找姜柟好好骂骂这贱人。
“魏夫人,郡王妃受了风寒,实在是起不来了,怕把病气传出来,不便见客!”李寒玥赶忙追上去,将人拦下。
“我身子骨好着呢,不怕病气!”魏郡公夫人来势汹汹,推开李寒玥。
“郡王爷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后院,魏夫人是客,应客随主便,无请硬闯后院,便是失礼!”李寒玥叫来几个看院的婆子,一起堵住了魏郡公夫的路。
“原来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啊?妾就是奴!你好大的胆子,也配跟我叫嚣?我今日来是看着郡王妃的面子上,你竟敢拦着我不让见?”
“还有没有天理了?你们郡王府才惹人笑话!改明儿,我非要让我家郡公参你谢霖一本!真是气死我了!”
魏郡公夫人肺都要气炸了,偏偏那几个婆子身强力壮,拦着她,完全没有进入后院的可能,只能叉着腰破口大骂。
“罢了!”谢霖硬着头皮,拉李寒玥离开,丢下一句命令,“来人!郡王妃身染恶疾,把院子给我看住了,谁都不许进来!”
南凌郡王府为世子大宴宾客,因为谢述是太子殿下宁愿颜面尽失,也舍不得摔死的孩子,又是皇后娘娘跟前新晋的红人,受邀的帝京勋贵无不到场祝贺,热闹非凡。
谁都想看看这位空降的小世子,有何过人之处。
水榭凉亭,前厅后堂,到处都是人,下人忙得飞起。
所幸偌大的姜家只派了姜淮前来,谢霖将老丈人请进主院书房,拿出了压箱底的字画。
姜淮一眼相中,爱不释手。
“岳父大人若是喜欢,拿走就是!”
“这如何能行?我岂能夺人所爱?”姜淮笑着摆手。
“您将爱女许配给我,我已感激不尽,这些本就是为了岳父搜罗来的!”谢霖笑着恭维,见姜淮一脸满意之色,叹口气。
他话锋一转:“不巧,柟儿水土不服,病倒了,实在起不来,我舍不得她操劳,便让她歇着了!”
姜淮笑意微收,默默将字画收起,装入盒中,淡声道:“人吃五谷,哪有不生病的?她既病了,好好休息就是!那这些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主要你祖父喜欢,他见了高兴!”
两人相视大笑,谢霖宽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