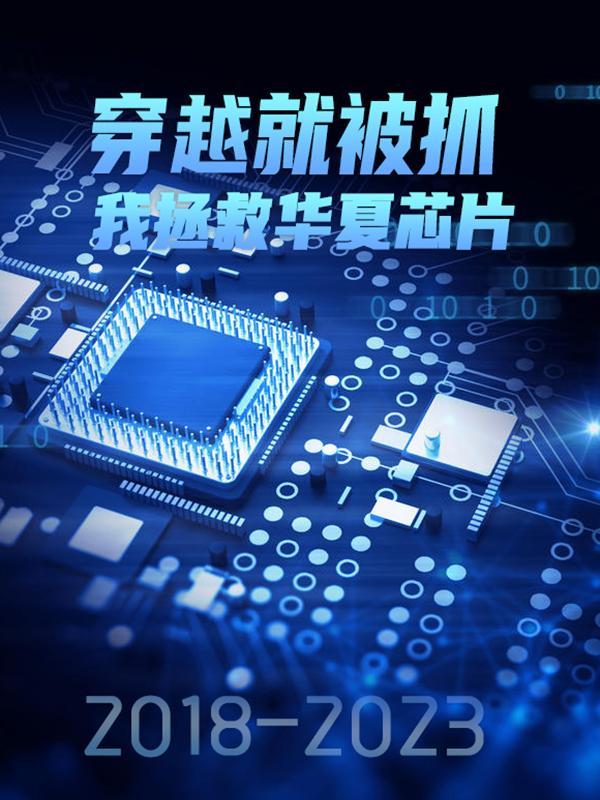笔趣看书>糖 > 第93页(第1页)
第93页(第1页)
景玉对这种安排并没有太多意见,一个人生命和精力都有限度,她注定没办法去经历所有的事情。也正因此,她很乐意倾听别人的故事,好像通过他们的交谈而短暂地接触到另一段人生。
德国整个白天的氛围都很闷,大街上人也不多。
但一到晚上,很多压抑的德国人都会借助酒来放松,或者说泄。克劳斯虽然不喝酒,但是他也盯住了景玉的酒杯,阻止她多饮,顶多尝个味道就移走。
八点钟一过,餐馆里气氛热烈起来,有个西班牙女郎装扮成吉普赛女郎的模样,跳着火辣的舞蹈,展示着自己的漂亮和热情。
她还会和台下人互动,只需要1欧,就能享受她亲自喂酒的服务。
1欧。
德国对难民开放后,给很多难民开出的工资,工作一小时,能拿到一欧。
这也是德国不够安全的因素之一。
在征得克劳斯先生同意之后,景玉兴致勃勃地出了1欧,享受到了舞娘的喂酒服务——用的是克劳斯亲自开封、倒出来的一杯酒。
舞娘没有立刻离开,她侧站着,向克劳斯先生伸出手,像一只慵懒、舒展身体的猫咪。
“您不需要来一杯吗?”她用英文问,“我可以免费喔。”
克劳斯先生礼貌拒绝:“对不起。”
舞娘笑起来,她抽了一张餐巾纸,在上面印下自己的唇印,手一扬,精准地落在克劳斯先生面前的桌子上。
“真遗憾,”舞娘眨眨眼睛,暗示他,“我就住在后面喔,今晚随时可以过来找我。”
克劳斯先生没有说话,他没有碰纸巾,侧身看景玉。
景玉手托着腮,手肘压在木桌上,正盯着他面前的纸巾看,抿着嘴,目不转睛。
克劳斯第一次见她流露出这种严肃的神情。
她看上去似乎很在意这张印着口红印的纸巾。
克劳斯倾身:“甜心,我——”
景玉却兴致勃勃地问他:“先生,您能帮我问问她,这口红是什么品牌吗?是哪个色号?”
克劳斯:“……”
克劳斯伸手,拍了拍景玉的后脑勺,抚摸着她绸缎般的黑。
景玉似乎听到他极轻地笑了一下,有些无奈。
也或许是幻觉。
克劳斯说:“我不会去找她。”
“您干嘛和我说这些?”景玉吃惊地睁大眼睛,“您该不会觉着我会因为一张印着口红的纸巾就介意、难过吧?难道您眼中的我气量这样小吗?”
“气量很大的小龙宝贝,”克劳斯耐心听景玉说完,手指顺着头下移,抚摸着她的肩膀,微笑着对她道歉,“抱歉,我知道你大概率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不开心,但我不想忽视你小概率存在的心情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