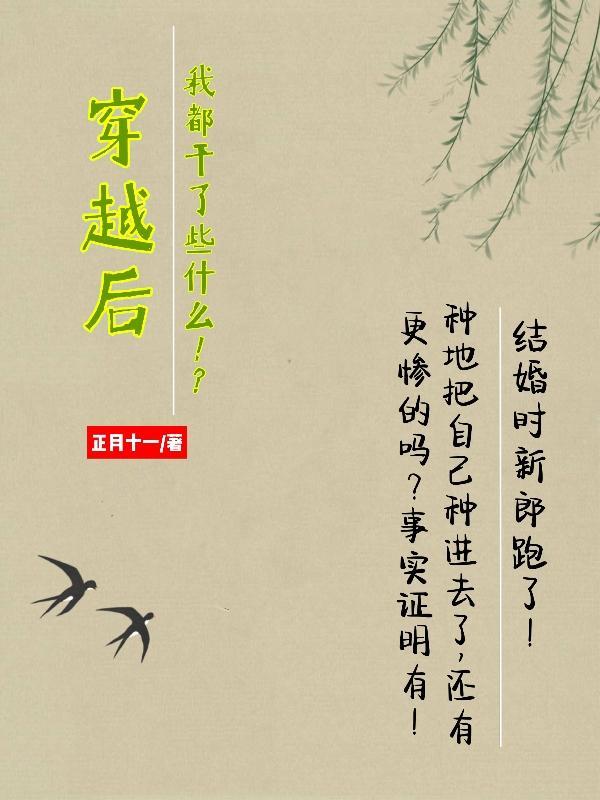笔趣看书>麟趾 梦溪石 > 第38页(第1页)
第38页(第1页)
杨钧絮絮叨叨,从鲁国公府大门口一直念到他那间胭脂铺子,又从铺子一路念到酒馆。贺融只觉得耳边有一万只苍蝇在飞,两耳被他念得麻木,连面部表情都僵了。“衡玉。”“三郎,你别不当回事,除了京城,你还去过哪里?你身体不如常人,万一路上病倒……你想说什么?”杨钧觉得自己真是操碎了心。贺融真心诚意地建议:“我觉得你经商太可惜了,可以考虑去兼任媒婆,保管三寸不烂之舌促成无数对金玉良缘,连朝廷都要给你颁一块御赐冰人的牌匾,自此流芳百世。”杨钧怒道:“我在为你烦恼,你还消遣我!”贺融拍拍他:“我知你的好意,但我在家已经被五郎念得两耳冒油,实在不想出个门也被人念叨了。”杨钧没好气:“你知不知道那些长舌之辈都喊你什么?”贺融:“知道,不就是贺三傻吗?”杨钧:“……”贺融:“这不正好?要是他们都觉得我不傻,以后我想坑个人,岂不很难?”杨钧:“……”贺融:“他们说我傻,无非是他们对突厥知之甚少,方才觉得可笑,若真有人与突厥完成差使,这些人又该换一套说辞了。”杨钧:“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路上遭遇不测?”贺融:“到时我已经死了,死人是听不见诋毁的,更是随便他们说了。”杨钧气结:“怎么横竖都是你的理?”贺融:“此事还未有定论,你现在操心过早,到了。”杨钧顾着说话,压根没注意看路,被他拉得急停脚步,茫然抬头。这是一间再寻常不过的酒肆,但因它座落在陶成子茶馆隔壁,连带生意也好了起来。杨钧皱眉:“你还真要请那酒疯子喝酒?”贺融嗯了一声:“我答应了的事,从来不反悔。”两人步入酒肆,堂子不大,一眼就能尽收眼底。昨日刚刚认识的那个薛潭,正坐在窗边,乐呵呵朝他们招手。对方留了一把络腮胡,把脸都遮去大半,唯独一双眼睛透着灵动洒脱,稍稍能看出些特质来。杨钧盯住他面前那几个酒坛子,一脸不爽:“我觉得他看我们的眼神,像在看冤大头。”二人走过去,薛潭还热情地起身迎接,对贺融笑道:“我等了你一上午,还以为你要食言了!”杨钧没好气:“明明说好请石冻春的,你却叫了双福到,待会儿我们可不会付账。”薛潭笑盈盈:“那也无妨,反正我知道三公子家住何处,到时候上门讨要酒钱就是。”杨钧跟人生意往来,也见过不少无赖厚脸皮,却没见过一个把厚脸皮发扬得如此光明正大的。他们俩说话时,贺融已自顾自倒了一杯,拿起来嗅了嗅,不明白为何有人如此嗜酒。他低头浅尝一口,微甜,但更多泛着酸,贺融是喜好甜食,但不喜欢酒水的味道,皱了皱眉,还是搁下。“你每次就这样醉醺醺地去当差?”贺融问道,有点不可思议。上回薛潭说自己是孟学士的学生,他就知道贺融一定会去打探自己的身份,闻言也不意外,笑嘻嘻道:“鸿胪寺差事少,我又不需要上朝,只要每日将差事完成便是。喝酒不会误事,多喝点有什么不好?改日我与三公子一道出使西突厥,路上若是少了酒,我还不习惯呢!”“……”贺融静默了好一会儿,确认自己的耳朵没有出毛病:“我何时说过要与你一起去西突厥?”薛潭挑眉:“你知道鸿胪寺典客署的职责吗?”贺融:“掌四夷朝贡,给赐送迎外宾,但东、西突厥不是外宾,也不会吃你这一套的。”薛潭有些得意:“我会突厥语,我敢说鸿胪寺中,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突厥习俗了。”贺融一怔:“就算如此,你为什么要去西突厥?人人都说我在哗众取宠。”薛潭:“我也听说了,他们还为你取了别号。”贺融:“……这句可以不用加了。”薛潭一笑:“听说陛下年轻时,性情外放,钟爱冒险,哪怕如今上了年纪,本性总还留着一些的,这等成败未知,火中取栗的建言,他十有八九是会答应,而且就算失败了,对朝廷也没什么损失。而我呢,我也想博一个前程,说不定将来还能留名青史呢?”杨钧撇撇嘴:“靠喝酒留名吧?”贺融看着薛潭,似在打量他的话到底可信度有多少,薛潭也不遮遮掩掩地任由他观察,一面举起手中杯子,主动碰了碰贺融身前的酒杯。“三公子意下如何?”贺融:“如果陛下答应了,我会请求陛下同意,带你同行。”薛潭咧嘴一笑:“多谢三公子,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连喝了贺融三天的酒,还特地往贵里点,贺融嘴上不说,心里其实还是有点心疼的,他刚拿了杨钧的分红,转头就要将这分红花得一干二净,要是薛潭言不符实,贺融想着到时候一定要让贺湛去把人揍一顿,让他还钱。好在薛潭的确是有点本事的,他从鸿胪寺中搜罗了一堆西突厥的资料,重新誊写一遍之后交给贺融。本朝建国之后,与西突厥从未正式友好往来,从前都是以打仗的形式来打交道,这些资料多是前朝流传下来的,因年代久远,很难辨别真假,薛潭特地将存疑的地方一一进行注解,又加上自己的想法,让贺融眼前一亮,觉得自己那几顿酒,总算没有白请。这期间,贺融让杨钧去打听薛潭家里的情况,这本不是什么秘密,杨钧很快就打听到了。薛家自前朝出了位名臣之后,子孙几代平庸无奇,加上改朝换代,薛家逐渐没落,到了薛潭父亲这一辈,已经是普通的耕读人家,别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祖上还出过这么一位大名人。薛潭自小顽劣,读书写字样样不行,撵鸡捉狗样样精通,到了十岁上,他的母亲去世,父亲又另娶了新人,后母生了儿子,薛父就将满腔父爱都倾注到小儿子身上,后母还打起让小儿子继承家业的主意,撺掇薛父与薛潭反目,薛潭年轻气盛,不愿将就憋屈,直接就摔门而出,分家自立。也不知是不是为了赌一口气,薛潭竟发愤图强起来,还考了进士,在鸿胪寺当官,这本是一桩美事,按理说薛父知道儿子这么争气,两人也该和好了。谁知薛家这一代祖坟冒了青烟,出息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薛家小儿子,也就是薛潭那个异母弟弟,比他还更争气,晚了薛潭几年考进士,不仅中了,还是头名的状元,如今在翰林院任学士,负责为天子起草诏书,可谓年少有为,春风得意。薛潭的继母也因此越发瞧不上薛潭,薛潭父子的关系自然没能修复,反倒更加恶化,在鸿胪寺也不像在翰林院那样被人看好前程,久而久之,薛潭还染上嗜酒的毛病,平日里出门都要带着酒气。这些事本不是秘密,当年薛潭的弟弟中状元,京里传得沸沸扬扬,都知道了他们家这段往事,许多人就像现在嘲笑贺融不自量力一样地嘲笑薛潭,说他不孝的也不在少数,这可能也是导致薛潭迟迟得不到升迁的原因。贺融大约知道薛潭为什么宁愿冒险跟他去西突厥了,无非是蛰伏许久,心头那一口气还没消。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浇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从某方面来说,贺融觉得自己跟薛潭,的确是有些相似的。皇帝那边的旨意迟迟未下,转眼就过了五月,时时有新鲜事物可以谈论的京城人,渐渐淡忘了这件事,连茶余饭后都不再提起。贺融并不着急,他依旧有条不紊地准备一切,他与薛潭讨论之后,都觉得皇帝极有可能同意出使的事,但天子有天子的考虑,所以还需要等待时机。这一日,正好夏至,崇文馆放了假,贺湛也轮到休沐日,兄弟几人听说京城东市有夏麦百戏看,就相约上街。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京城人的热情,小小一个夏至,也非中秋元宵那样的大节,街道上居然也接踵摩肩,人山人海,两旁的小摊贩挂满了五色粽子和麦穗,还有的在折扇上画满各种奇趣图案,吸引小孩儿驻足观看,目不转睛。因时下还有在夏至吃饼吃面的习俗,那些食肆面摊更是将这种热闹发挥到极致,打卤面、炸酱面、麻油拌面,各式鲜香在空气中混杂,哪怕原先肚子并不饿的,也不由得要咽口水。更不要说还有各种去上香的,祭祀的,走亲访友的人,几乎将所有街道都塞得满满当当,挤不出一点缝隙来。贺穆他们万万没想到京城的夏至会是这等场景,印象还停留在竹山县时过夏至的情形,家家户户顶多应景吃一碗面之类,几个人原是走在一块的,结果一不留神就被冲散了,余下贺湛挂心贺融腿脚不便,紧紧拽着他的胳膊,这两兄弟侥幸还在一起。勉强挤到一块还能喘息的角落,贺融忍不住出了口气,刚刚人群一番推搡拥挤,让他额头上都冒了一层薄汗。“还好出门前顶住嘉娘的央求,没带她出来,不然肯定是顾不上她了。”他对贺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