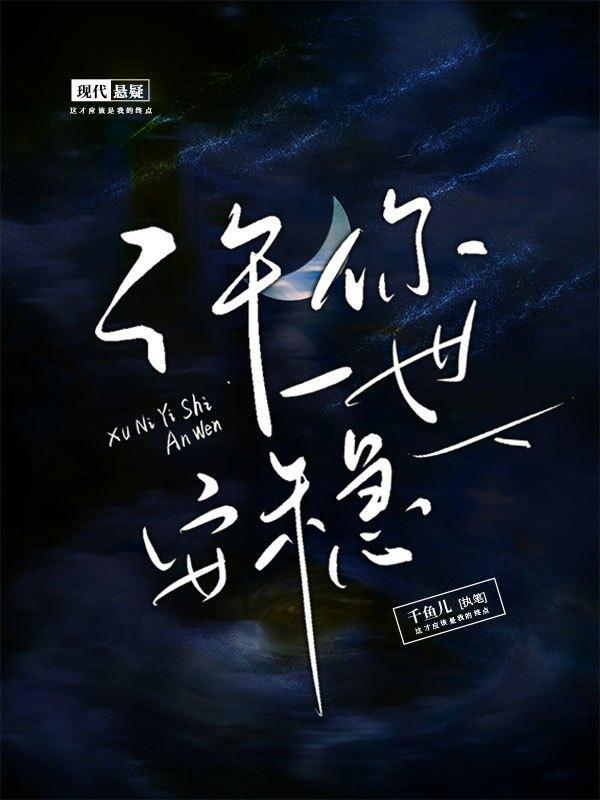笔趣看书>金鹧鸪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 第26頁(第1页)
第26頁(第1页)
「綏綏姊姊,我沒有……我不是不回家,是實在回不去,姊姊,我坐過牢了,至今還有人追殺要我的命,我不能連累你們呀——姊姊,我姊姊現在還好嗎?你們怎麼也到敦煌來了……」
綏綏下意識放開手,忙又捂上了他的嘴,驚恐地睜圓了眼睛低聲道:「坐牢……為什麼坐牢?你幹什麼了!」
「沒有!沒有!」阿武掙脫開她的手,急促地小聲道:「我什麼也沒幹吶,綏綏姊姊,是寶塔寺的那些和尚——我到了隴西,想和一個朋友借些錢來倒騰蘋果賣,簽了他們五十貫錢的契約。那些殺千刀的坑我們不識字,害慘了我們,稀里糊塗就簽了高利債,我們還不上,只好把自己抵押給他們。好多人都是這樣……地沒了,人也沒了,後來有人鬧起來,要滾釘板告到知府衙門上,說人越多越好,我也跟著去了,可不知怎麼著,反被他們抓了起來……綏姊姊,你信我,我真的什麼壞事都沒做過!」
綏綏也懵了,不知該不該信,平了平氣息,又問:「那、那你是怎麼出來的?」
「去歲隴西一帶地震,皇帝為了祈福,特赦了一批犯人。我們雖出了獄,卻得罪了寶塔寺,我那朋友就被他們殺了,我一路逃到敦煌來……怎麼敢去找姊姊!」
綏綏緊緊盯了他一會,咬牙小聲道:「罷了……看在你姊姊面上,我就信你這一次!如今我們住在西市小花枝巷裡,今晚你先回住處,在外面晃蕩兩天,挑個晚上來找我們,別讓人看見了。」
小廝打水來了,綏綏把他推到了屏風後,自己遠遠坐到了窗台上,背過臉道:「快洗個澡吧,我不看你。」
說來也怪,翠翹已經是個清麗佳人,阿武一個男人,竟比她姊姊還美十倍。灰頭土臉的時候還不覺得,待洗去了滿臉污垢,白白淨淨的,一雙烏黑的大眼睛,比李重駿還亮,長發隨便一紮,身上的破衣服也被襯托得俊逸起來。
深夜的時候,綏綏打發阿武先悄悄下了樓,管事的見了都目瞪口呆,只恨自己沒發現這塊璞玉,早知就該收入麾下,讓他納賓接客。
綏綏結帳之後,也趁著夜色溜出了南館。
兩個恩客模樣的漢子在樓下吃酒,一臉茫然地看著另一個,低低道:「阿成,咱們這……也要稟報殿下知道嗎?」
另一個也很為難:「不、不用罷,殿下才到隴西,正煩著呢,還是別去觸這個霉頭。」
兩個侍從本想著就這一回,綏姑娘又沒危險,瞞過去了,誰也不會知道。可過了兩天,他們卻發現大事不好了——
一日夜裡,那少年竟鬼鬼祟祟到了綏綏家後門,敲了兩下門。綏綏打開門,二話不說就把他拽了進去。
從此……再也沒出來過。
半月之後的隴西衙門,侍從阿成從敦煌來,照例來向魏王殿下稟報。
這要是高閬在,一定要先仔細盤問一遍,再囑咐他該如何說,但今天高閬不在,只有高騁守在門外。
高騁本就有點木木登登的,不大通人情,請示了李重駿,便直接放了阿成進書房。
李重駿在堂屋裡看卷宗。
天暗,房間又大,大夏天也感到寒涼。他穿著黛藍的襴袍,俯身站在案前,一張長長的捲軸攤開,一手撐在案角,一手執筆,似乎在凝神寫什麼。
聞聲抬頭,神色沉靜,像浸在冷水底的白玉。
阿成道:「在下見過殿下。在下來也無甚事,綏姑娘那裡……」
他真不知道怎麼開口,遲了一遲,李重駿已經皺起了眉。
阿成忙道:「綏姑娘很好!就是、就是家裡如今多了一個人……」
李重駿挑眉。
阿成一咬牙:「上次姑娘去北里的南館吃酒,在那兒和一個……一個送水的小子,歇了半宿。後來,那人就住進她們院子裡去了……」
他忙低下頭,根本不敢去看李重駿。說著說著,只覺得渾身汗毛倒豎,底氣也越來越弱。
可直到完全閉了嘴,李重駿也沒說話。
詭異的寂靜,簡直像鈍刀子割肉,好在這時候又有個侍衛進來,匆匆行了一禮便道,
「殿下,找著了。五年前那些被關進牢獄的人里,除了病亡的,自盡的,就是挨到去年放出來,也都被寶塔寺的人殺得七七八八。終於找著一個,逃到敦煌才躲過一劫。他在敦煌流落了好些日子,一直靠送甜水過活,在下追查到北里的一處南館,掌柜的說是半個月前最後見他,一個賣酒的年輕商人包他睡了半夜,看樣子,他也賣身。後來便不知所蹤了,在下想請殿下多派些人手,在敦煌仔細搜查一番——」
打斷他的是一聲碎裂的脆響。
阿成抬頭,只見那根烏木白銅的筆桿已經折斷在李重駿手裡。另一個侍衛嚇得住了嘴,茫然地看看李重駿,又看看阿成。
「不必了。」
李重駿直起身,把手上的殘骸丟在桌上,閒閒擦掉手上的墨跡:「我們不是已經找到了麼。」又叫阿成道,「你帶著他們,去到小花枝巷,把人帶來。」
他臉上沒什麼表情,唇角卻是仰著的,極其詭異的弧度,似笑非笑,讓阿成毛骨悚然。
第二十四章吃醋
綏綏是送酒回來的路上被「請」上馬車的。
說是請,簡直和搶差不多,一輛馬車在巷子口攔住她,下來兩個大漢,說有人「想要見見她」,雖然行了禮,但也沒有給她任何拒絕的機會。一左一右堵著,幾乎是挾持著她上了馬車。
小貼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1t;)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