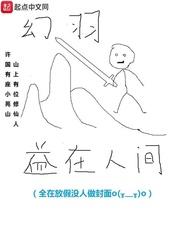笔趣看书>我的危险性竹马 > 第32章 第 32 章(第3页)
第32章 第 32 章(第3页)
“洗完去泡露天温泉,延儿去哪个,他就跟着下哪个,后来在更衣室把他堵住了,”卓望道讲到这儿来就开始自顾自笑抽,回回说回回笑抽“你、你他妈知道那个人干了什么吗”
安问心想,是不是卖小黄碟的啊,还是卖那种偷来的二手手机二手名表的
任延不动声色深吸一口气,听着卓望道揭晓这个烂谜底“他二话不说跪下就想给他口。”
安问“”
他睁大双眼,因为这当中的画面感太过有冲击力,以至于他的瞳孔都微微扩散。
什么东西
“干,”任延骂了一声,“你能不能别说得这么恶心,他是先问我,玩不玩,然后才想蹲下拉我裤子,但是我他妈把他拉起来了好吗”
“我才干,你还好意思说,”卓望道一边笑抽了一边骂“我早就看他不对劲,不然我跟你一起进更衣室干嘛关键是他跟你说玩不玩,你还没反应过来。我跟说你当时就是危险,知道吧,差一点你就贞操不保了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纯呢”
“我他妈”任延拧起眉烦躁道“行了说完了下次别说了”
“经典咏流传,我他妈能说到你结婚,知道吧,等你结婚那天,有请伴郎团代表言,到时候我就给你现场来段单口相声,怎么样”
“你特么找削吧”任延想揍他,卓望道拿淋浴头防卫,“别过来啊,过来我滋你。”
安问抹了抹脸,看着任延,比划了一下“那后来呢”
“后来没有后来”
卓望道仰着脖子“后来就是延哥说再他妈多看一眼几把剁碎”
安问猛然想起了在卓望道出租屋那一天,任延洗完澡出来,难怪反应这么大,原来是有心理阴影。可是他又不怕卓望道看,干嘛单单对他防备想到这一层,安问忽然悟了,眼睛瞪大不敢置信难道任延觉得他是变态所以要防他
谁才是变态啊他可不会闻别人头动不动就想牵手,还、还随便叫人宝贝
任延浑然不觉他想歪到了十万八千里,只觉得脊背一凉,扭头过去,看到安问委屈凶狠眼睛瞪瞪像铜铃。
总不能真在这四面漏风的浴室把话给聊透了,任延走过去,无奈地在安问头上揉了一把,“外面等你。”
关了浴室门,仰靠在门上长出了一口气。他出来时安问还没脱衣服,幸好卓望道是个八百度近视,否则任延不保证自己不会嫉妒疯到想把他眼睛给挖了。
他没回房间,去院子里透了透气,男女寝室和护工房间都已经熄灯了,只有二楼兰院长的卧室灯还亮着。
寂静之中,阴影之
下,这里贫瘠的一切,如同一幅静物油画般一览无余、无处掩藏。
操场是黄泥填的,下了雨,恐怕就泥泞得不能下脚。秋千是用废汽车轮胎做的,单双杠都已经生锈掉漆,围墙脆弱得似乎一推就倒,石砖灰泥的厨房已经可以被判定为危房了却还在使用,墙角堆着高高的木柴,很难想象二十一世纪还有地方别说燃气了,竟然连煤气、煤炭都还未使用上。
与之相比,校舍和宿舍是难得的整洁,可见福利院的所有资金应该都拿来修葺和维护这些了。
安问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的。
无人问津、如同被全世界遗弃,只有一只小熊自始至终,从新鲜抱到破烂。
任延转身向二楼走去。
虽然知道了安问在福利院成长,但来到这里之前,任延的脑子里出现的,都是西方高福利国家的福利院,有宽敞的绿荫草坪、整洁的白色大楼、定期的慰问娱乐,稳定的慈善捐赠,细致的生活料理,以及周到的人文关怀。
作为安远成儿子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跟这里扯上关系,他应该跟卓望道一样,如果不是这样的机缘巧合,那么便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世上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兰琴因的门关着,任延敲了敲,礼貌地问“兰老师,您睡了么”
椅子被推开,过了会儿,兰琴因打开了房门,身上裹着一条起球飞边的薄毯“我一猜就知道你总要找我。”
她让出身,任延勾了勾唇,说着“打扰了”,走进屋内。
兰琴因拂了拂床尾,请他坐。
“我年轻的时候,从前苏联留学回来,工作、下乡、结婚、离婚,医生说,我生不了孩子,”她在任延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戴起老花镜,笑了一笑“可我喜欢孩子啊,中间又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总而言之,我到了这里,收养了几个被遗弃的孩子,慢慢的,就有了这个既不正规、手续也不齐全的福利院。
“你应该也观察到了,我们很穷,这里有的孩子是有先天性疾病的,比如跛足,比如兔唇,或者六指、口吃、智力障碍,有的呢,很健全,但家里太穷了,父母养活不了,知道我能给他们一口饭吃,找地方上学、找体面人领养,于是就把孩子用破布一裹,扔到我门口。
“问问,是唯一的例外。他知道自己叫什么,知道自己家在哪儿,小小年纪会背唐诗,穿得也好,教养也好,长得呢,也挑不出错。他来的时候五岁,坐小汽车来的”
任延忍不住打断她“送他过来的女人,是不是姓琚名琴”
“我不知道。”
任延愕住“你不知道”
“他不是被特意送过来的,是经过了这儿,是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托我暂管。”
“暂管”
兰琴因笑了笑,伸出手指“三天,只托我照顾三天,但我照顾了十年。”
安问洗完澡,去卓望道他们房间吹头,任延正坐在桌前写题,但摊开的物理卷子只刚写了第一道解答题。
错了。
安问扔下半湿的毛巾,从任延手里抽走笔,继而趴在他草稿纸上,将原来的步骤划掉,重新代了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