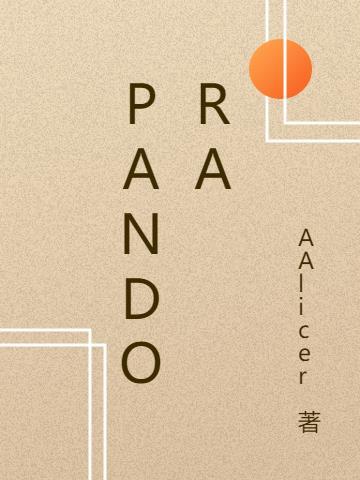笔趣看书>重生之佛系谋反 > 第44章 自为国贼2(第1页)
第44章 自为国贼2(第1页)
建康有两处码头,一个是城南朱雀桁外的青溪渚,一个是城西石头城旁的石头津大埠。
青溪渚码头豪华,水质清澈,所停泊多为世家大船和官船。
石头津大埠河道宽阔,江水滔滔,可容纳几万船只停泊。往来多为商船、货船,民用客船,码头上三教九流,贩夫走卒,熙熙攘攘,可谓龙蛇混杂,泥沙俱下。
这日正午,大埠如平日般舳舻往来不息,桅杆如林,舟楫塞道,商民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人群中出现两位布衣,一位身材高大,似是北方来的商人,一位中等身材,也似北方侠客。
若在别处,自可注意到二人气度不同凡俗,但在大埠码头,再怪异的人也不会让人太过好奇关注。这里往来奔波者东西南北各地人都有,都是辛苦讨自家生活的,没那么多闲心关注别人。
崔懋不喜欢大埠码头,不喜欢这么多的南朝人,更不喜欢靠着水。
但他是南朝之客,只能客随主便。
崔懋上了一处小客船,客船离开码头,驶向远处另一处泊位。那里停泊着一只普通的小客船。崔懋踏着渡板过船,弯腰走进狭小的船舱中。
崔懋脸上阴晴不定的打量眼前的南朝皇孙萧黯,如同初见印象一样,仍觉得此少年甚是神秘。
他布帻布衣,打扮颇像寒士更似家奴。南朝人向来注重身份礼仪,何况是皇室郎君。他如此打扮若被现当被有司弹劾,严重者,有夺爵免官之祸。
他如此涉险来会,所求自然是大干系之事。
那边萧黯开口了“今日,请先生来此地,是想谈桩买卖。”崔懋没有接话,静待对方下文。
“那府里贵人出什么价钱,我便出什么价钱,只是,给他的货也要全部交割给我。”
萧黯语气平静,与虎谋皮。
崔懋也不动声色道“我不明白七郎之意。我所求是从官司中脱身,让那人也从官司中脱身。如果七郎答应,从此南朝无崔氏只字片语。”
萧黯知道,崔懋与萧正德结交为时不短,彼此应也是为对方投资过大本钱的,彼此有信,难以舍弃。他唯有断了崔懋的后路,再许之以诚。
“先生刚刚说出的诉求,放眼京城,唯有我能予你。我知道先生还有未说出的诉求,那人如今已是众矢之的,日暮西山,已无能给你,非我夸大,放眼京城,仍唯有我能予你。”
崔懋心念一动,目光闪烁。
他何尝不知道临贺王如今已被昭明太子诸王盯住,且日渐失去皇宠,但数年经营,好不容易在南朝宫廷找到同盟,如何能舍。再说,眼前这少年,是天子嫡脉,如何敢信他能为东魏谋利。
崔懋道“七郎多虑了,我所求只有这些,我所能给予七郎的唯有约束家族。”
萧黯目光温和如烛火,如闲话家常般道“先生与家妻是族亲,家妻是东魏人这件事,若在京城翻起,最差结果是我无缘高官,但更大可能是圣命我们两家和离,反倒于我前途无损。因我与家妻自幼相识,有百年之约,不愿背信,故而才有当日之请。
那日我非妄语哄骗先生,家妻身世确实关乎先生使命。
我确也善卜筮,我不但知道先生善做买卖,还知先生有通天的本事。我所求不多,即是在皇太子登基后,我与兄长俱可偏安某州。不巧,我看中的是与贵国接壤的南兖州。”
萧黯将心思已和盘托出,一双眼睛盯着崔懋,目光仍旧温和,却洞察微毫。
崔懋感到巨大的机缘和危险同时来临。他与对面的少年对视,他在对方目光中看到真诚,然而多年的谨慎使他不敢轻易答应。
崔懋道“若七郎让我与那人脱身,我会游说那人放弃南兖州,尽由七郎去运作谋取。”
萧黯没有满意,也没有露出讽刺或冷笑神情,只是平静道“我对君坦诚,君却对我矫饰。倒是我看走了眼,原来君并无影响南北两国国运的胆识。请君走好,恕我不送。”
崔懋愣了片刻,起身告辞。
萧黯看着崔懋走出船舱的背影,心中焦虑。此人没有就范,或许他心内已有动摇,但仍需时日决断。想是在这过程中,至少是暂不会将崔氏家事这把柄毁弃。
萧黯心内稍稍轻松了一些,忽一日,武三来报说崔氏约见。
萧黯猜想已近成事,答应约在钟山故园见面。
仍是山脚下树林中的瓦舍草堂,萧黯仍是竹冠布袍的道士打扮,静待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