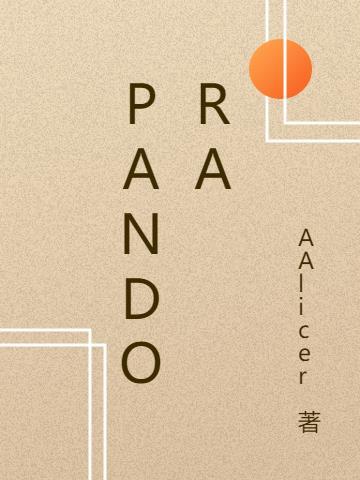笔趣看书>重生之佛系谋反 > 第93章 出国度蜜月(第1页)
第93章 出国度蜜月(第1页)
冀州东海郡与郁州两郡历来是南北朝相争之地,在本朝也数次南北易手。
如今,东海郡归南朝冀州治下已有二十年,其田地大多是军屯田,籍民大多是军户,然而,二十年无战事,农耕安逸,军民不分。
东海郡边境口岸北关镇,平静得不像边镇。
南北往来,水路自彭城过境,6路常走北关。
水路都为大商人,虽通行频繁,但并不会深入东魏内6太远,一般在定陶倾销即返。
6路一般都是小商人,小本买卖,为求利润,常深入东魏内6贩卖。
南朝商人贩去北方的货物,最多的是丝绸,另还有漆器、木器、金银铜錾刻花雕镂刻器皿,茶叶、香料,珍珠、珊瑚等也有。
这一日,在众多自北关过境的商队中,有一支不起眼的队伍。
肥壮走马拉着两辆主从暖车。长行大青骡拉着三辆货车,装的是材质中下的绸缎和少量绵絮。另还有一辆杂物车。数名家丁骑马前后跟行。
若说这支商队有什么特别,或许是队伍中有两匹高头大马坐骑。一匹枣红,一匹青骢,两匹马毛皮闪耀,膘肥体壮,四肢筋骨有力,双目明亮,一望可知是两匹相当难得的良马。
家主手持淮南庶民赵氏身籍和行商文牒通关。
过关后,萧黯与笼华夫妇二人踏上东魏济州琅琊郡的地界。
他们轻装简从,萧黯只带武三等数位武士,笼华只带了隐露和长信夫妇。
如寻常南朝商队一样,只走官路,遇官障捐钱,见官爵避道。
一应答问往来都是武三和长信两个出头,无论官民询问,都说是前往黄河边的齐州历城贩卖货物的。
东魏官民对南朝人并无恶感,偶有盘查,似也是警惕防备西魏人混入。
暖盖主车内,夫妇并肩而坐。
萧黯头戴平上帻,上穿绛红粗布短衫,下穿皂色束腿夹绵裤。如北地男人一样,并未穿下裳。衫裤外直接穿交领窄袖两片式夹绵粗布袍。脚穿牛皮高靴。
这打扮类似南朝的骑猎冬装,在北地,不过是寻常殷实家主的打扮。
笼华头梳平髻,插木笄,戴绢花,配粗布暖额。
她上穿绛色粗布衫、下穿皂色绔裤,外罩窄袖过膝短襟夹棉粗布袄,露出半截下裳厚布褶裙。脚踏牛皮小靴。
这打扮也是寻常北方殷实人家主妇的打扮。
然而,即使两个人打扮的再像北方平民,一口的江南官话仍会暴露出籍贯。
细嫩的双手,干净的肤色,也能看出他们并不是寻常人家的操持者。
萧黯看笼华双眉修长,明眸清澈,唇红齿白,天然可爱。
虽然她身量甚高,风骨利落,又打扮成北人模样,可是莹白纤细,眉清目秀,一看就是江南女子,并看不出半点北地人血统。
可见,造就人的不全由血统,更赖经历和见识。
想笼华前世,在东西两魏漂泊游历,嗓音毁坏,皮肤被日头风沙磋磨的粗糙,举止如男子,经历了许多风霜苦楚。数年后,他们再度见面时,她的目光沉静沧桑,气质冷漠坚硬,性情锋利固执,与少女时判若两人。
在她最艰辛的那几年,他没有在她身边。
在她的心中,那些伴着她飘泊各地的朋友和侍从,都很重要,在某些时刻,甚至过了他。他嫉妒,也自恨。
这一世,萧黯不想错过什么,他会陪着她去拜祭她生身父母,共同游历南北朝,共同经历一切。
笼华并不知萧黯的心事,只一派天真兴奋,进到一县城,不顾冷风渗入,只撩起车窗,不住的看向窗外人行。
原来,北地的妇女,不论身份,行走不避,还能看到身着暖裘的贵妇率众骑马而行。
妇人们莫说与丈夫同车,就是与丈夫并肩步行,并肩骑行的也常见。
笼华想,这胡人不讲究礼法,果然活得更爽快。
萧黯偶尔也看向窗外,心中想的是,这琅琊郡的城池、建筑、风土与淮北并无大不同,但人的装扮却迥然,汉人衣冠大改,胡风大盛。
琅琊郡本是南朝第一门阀王氏的祖籍,南朝曾多次试图夺回。
然而,山东乃士族之本,此地也是北朝门阀公卿的祖籍,且是东魏心腹之地,对方自然也誓死扞卫。
说来自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士族的根就断了,便是在南朝安置了无数侨州、侨郡、侨县,何曾是故土。
便是自家萧氏的祖籍,也在东魏山东兰陵郡,所谓的南兰陵的祖籍不过是安慰自心罢了。
乱世之下,士族庶族经历的是同样的离丧。
数代人的血泪之下,天下三分。
如今,富饶的南朝,无论公卿庶民,好像都已忘了自己曾经是无家可归的北怆。
直到,乱世再度来临,又是无数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幸存者待收拾了残破河山,两三代人之后,又再度忘了旧事,重新安逸起来。
萧黯想,自己拼尽全力,或者可以避免这十年的丧乱,那么下个十年,二十年呢,江南能偏安几时。